(一)道德与利益可以统一
企业是一种功利性组织,并不意味着做企业可以不讲道德与道义。
自古以来,无论是在东方,还是在西方,都有轻商贱利的传统。中国有“为富不仁”、“无商不奸”的说法,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“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”的论述。人们之所以轻视商业,是因为他们认为道德与利益相冲突,二者不可得兼。道德与利益真的不能兼顾吗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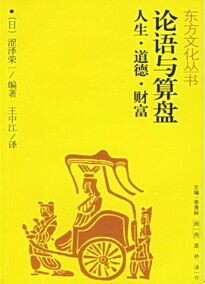
涩泽荣一认为,“论语中有算盘,算盘中有论语”。
涩泽荣一是“日本实业之父”,同时也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。他认为,要发展资本主义,就必须改变轻商贱利的传统观念。
在书中,涩泽荣一将《论语》和“算盘”统一起来,提出了著名的“论语加算盘”学说。他认为,“论语中有算盘,算盘中有论语”,即讲道德、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,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、讲信用。他这样论述“公与私”的关系,所谓公益与私利本为一物,“公益即私利,私利能生公益”。他说:“抛弃利益的道德,不是真正的道德;而完全的财富,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。”涩泽荣一将道德与利益统一起来,对后世的日本企业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稻盛和夫是当代最富传奇色彩的日本企业家,他一生曾缔造过两家世界500强企业,其经营之道广受中、日企业家推崇。稻盛先生毕业于鹿儿岛大学工学系应用化学专业,学习的是与药物学相关的有机化学,他的第一份工作则是从事陶瓷和绝缘体的研究,这属于无机化学的范畴。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经营管理知识背景的经营管理大师,在日本被誉为“经营之圣”。
1959年,27岁的稻盛和夫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时对经营知识一无所知。他这样回顾创业之初的心路历程:“当时并不知道什么叫经营,对经济知识和企业会计更是一窍不通。然而,一旦开始开展事业,我这样无知的人就将面临一个又一个的必须作出判断的问题。我的公司是一个只有28名员工的小公司,各种各样的事情不断涌来,需要我决定:这件事情怎么办?那个事情如何搞?我即便是没有经营的知识和经验,但作为经营者,却必须对员工的提问作出判断,而判断的基准应该放在什么地方,是让人烦恼了很久的问题。当时,我们的公司是一个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就会散架的小摊子,如果自己的一个判断失误,公司就会瓦解。一想到此,我就担心得数夜不能入眠。”
后来,经过很漫长的思考,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。他想:“既然对于经营我一无所知,那么不如回到原点。”是非、善恶、公平、正义、诚实、博爱,这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,是孩提时代父母和老师天天在教导的道理。自己虽然不懂得经营的道理,但做人的常识还是知道的。如果以此作判断基准的话,那么他是清楚的,也是能够掌握的。自此,他把“作为人,何谓正确”当作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,“把作为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”。他将从这一判断基准引发的思考,不断地记录到笔记本上,日积月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经营哲学。

稻盛和夫把“作为人,何谓正确”当作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,日积月累形成了
自己的一套经营哲学。
稻盛和夫认为,“人们的思维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判断标准。一个是按照‘得’、‘失’来进行判断,另一个是按照‘善’、‘恶’来进行判断。我的判断标准,不是按照得失,而是按照善恶。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标准,我是基于这个标准来开展我的工作的。”他在总结一生的经验教训时说:“现在回想起来,不是依据经营的经验和知识,而是以这种最基本的伦理观、道德律为基础去从事经营活动,正因为如此,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。”在他看来,良知和道德是经营管理决策的终极依据。
在中国人潜意识深处,道德与利益好像总是相互冲突的,不能兼顾的。似乎是做好事就一定会吃亏、受损失,做坏事就一定可以沾便宜、得好处。但事实上,道德、智慧和利益在绝多数情况下是高度统一的。弗兰西斯·培根说,知识即力量。但苏格拉底也曾说,知识是美德,智慧即至善。有大智慧的人不会做错事,更不会干坏事,并且总能建功立业,成就大事。
(二)做企业不同于做生意
当然,做企业又不同于简单的经商或做生意,企业家也不同于生意人或个体户。
经商或做生意的核心命题是找到贱买贵卖或者说价格差的机会。所以成功的商人都擅长揣度人的心理以进行逆向操作,所谓“旱则资舟,水则资车”,或“贱取如珠玉,贵出如粪土”。做企业的本质使命则是要把市场或顾客创造出来。这就要布一个很大的“局儿”或者做一个很大的铺垫,以突破各种市场障碍,从而奠定与顾客持续进行交易的基础。同时还要建立竞争壁垒,以使竞争对手无法模仿,不然经营活动就难以持续。这一过程可以用“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”或“前人种祸,后人遭殃”来形容。所以,做生意更多地关注“一次性地赚点钱”,而做企业则要“连续不断地赚钱”。
个体户是一个人赚钱,而企业家则是带领一群人赚钱。对于生意人或个体户来说,“做什么”、“怎么做”是他们自己的事情,无需让别人知道。对于工商企业来说,“干什么”、“怎么干”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说法;这套完整的说法,管理大师彼得·德鲁克称之为“事业理论”(The Theory of the Business)。企业家不但自己要深入思考企业的事业理论,而且要向组织成员详细解释企业的事业理论。只有这样,才能统一全员的意志,形成上下一致的步调;才能统筹前后的行动,不致出现“自己的脚绊了自己的腿”的现象。
生意人的信条是“什么赚钱干什么”,他“一段时间只能从事一笔买卖,而在从事另一笔买卖以前必须把前一笔买卖完全清理掉”。企业需要超越一个人抑或一代人的生命局限,它必须“把资源投入到一个无限长期的未来”。企业的今天既是它昨天发展的结果,但它又要承担为明天发展打下更坚实基础的义务。因此,生意人如同到处寻找猎物的猎人,他是机会导向的。企业家如同春耕夏耘期盼秋收冬藏的农民,他是战略导向的。
(三)企业人也绝非经济人
经济学把人视作经济人,认为人“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,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”。既然人都是经济人,那么人的个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经济学在把人的个性抽象掉之后,把人都归结为劳动者,进而把他与土地、资本并列、并称为生产要素。经济学是见物不见人的一门学科。
近代会计学曾把人视为成本或资本,近代的管理学也曾把人视作资源或资产,于是就有了人力成本、人力资本、人力资源以及人力资产的概念。这些学科唯独没有拿人当作人。既然你不拿别人当作人,别人也就不可能拿你的事当作事,所以就会有“出工不出力、出力不出活儿”的事发生,于是就有了福特式的抱怨:“本来只想雇一双手,每次来的都是一个人!”
其实,人的本质只能用“人”来表达,或者说他主要是社会人。是“人”,他就不可能是“物”,其他的表述诸如生产要素抑或资本、资源或资产等都是片面的。人不仅是理性的,也是感性的。人不仅有利己的需要,而且也有利他的需要。人不仅有物质需要,而且也有精神需要。人不仅是自然人、经济人,而且也是社会人。很显然,仅靠经济利益刺激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,人还有情谊、公平和成就的需要。松下幸之助说得好,工作不只是为了挣取那份工资,也是为了挣取一份人情义理。
中国二千多年前的先哲孟子对于人心有着深刻的体察。他有一段话:“口之于味也,有同耆焉;耳之于声也,有同听焉;目之于色也,有同美焉。至于心,独无所同然乎?心之所同然者何也?谓理也、义也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嘴巴对于味道,有相同的嗜好;耳朵对于声音,有相同的听觉;眼睛对于颜色,有相同的美感。一说到心,难道就偏偏没有相同的地方了吗?心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?在道理,在义行。孟子坚信,追求真理、道义是人心中共有的东西。
(四)企业也是一种道义性组织
卢作孚是中国近代实业巨子、民生实业公司创办人,他曾这样定位自己的企业:“个人为事业服务,事业为社会服务;工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,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,而民生公司就是这样一种超个人成功的事业,超赚钱主义的生意。”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说:“只有能将义旗举起来的人,才称得上是企业家。这里的‘义’,也就是办企业的终极意义。”不讲道德的企业终将被社会抛弃,不讲道义的企业也难以凝聚人心,一群乌合之众、一帮蝇营狗苟之徒绝对成就不了伟大的企业!
人有多面性,企业也有多面性,把它们归结为一面,在理论上会导致偏颇,在实践中会招致碰壁。在企业内部成员之间,除了经济利益,也是有道义存在的;在企业的现在与未来之间,除了赚取利润,也还有原则存在的。企业不仅是一种功利性组织,而且也是一种道义性组织!


 高可为
高可为

